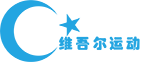亲爱的妈妈,自您2017年4月25日,最后一次电话里告诉我:“孩子,再不要给我们打电话。”之后,今天已经是1095天了,已经是整三年了;妈妈,至今,您的话音仍在我耳边回响,您的哭声还在耳边;从声音,我感觉到了您的恐惧;当时,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感觉到了您们正在遭遇着前所未有的迫害。
亲爱的妈妈,自您2017年4月25日,最后一次电话里告诉我:“孩子,再不要给我们打电话。”之后,今天已经是1095天了,已经是整三年了;妈妈,至今,您的话音仍在我耳边回响,您的哭声还在耳边;从声音,我感觉到了您的恐惧;当时,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感觉到了您们正在遭遇着前所未有的迫害。
亲爱的母亲,当我们于2001年在德国见面时,还记得您说的话:“孩子,我们已经活够了,该见得也都见过了;除了安拉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走你选择的路。”这些年来,警察的骚扰,政府的迫害,您都昂首挺胸熬过来了,从未犹豫过;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您的恐惧,那是个什么样的迫害能让您如此恐惧,亲爱的妈妈?
亲爱的妈妈,三年前,尽管我和父亲两三天通一次话,但和您我几乎是每天通一次话,我们有说不完的话;对我,妈妈,您不仅只是慈祥和蔼的母亲,您还是我的启蒙老师、师长、价值观导师、可以谈心的人生伴侣。
1982年,我刚刚开始懂事,我就离家到和田市学习伊斯兰教;自此,我没有能够在您身边,帮您做一些最简单的家务;后来,我为了继续学业,想要出国,是您们把家里的全部积蓄拿出来,于1986年3月13日把我送上了海外求学之路;我在埃及学习的那4-5年,您承受了无尽的思子之痛。
妈妈,正如您后来知道的,1989年,在朝觐期间,我们在埃及学习的维吾尔学生和在巴基斯坦学习的维吾尔学生聚集在阿拉法特山展开 “怎样做,对祖国的贡献最大“的讨论;最后,我们总结如下:如果我们完成学业回家,可能面临两种选择;一,走真正的真主之路,很快被抓入狱;另一是放弃走真正真主之路;两种选择都无法为民族服务;那怎么办呢?答案是:向西迁徙。这样,未经您的允准,我擅自做主,于1990年9月9日和同伴们一起来到了德国。
由此,我迈出了“为祖国,不得不暂时离开祖国”征程的第一步;伴随思念,尽管和您的距离越来越远了,然而和您的心里距离却越来越近;因为母亲,越是远离祖国,我发现,您越来越成为祖国的象征;使我更加向往祖国,更想知道和了解祖国;也使我常常投入寻求解救祖国之路的沉思和寻觅中。
亲爱的妈妈,那一天当您说:“再不要打电话”时,我和其他亲人的联系早已中断一两年了,至此,和您的联系也断了;放下电话,我呆站着,头晕,眼含泪水;似乎和您就此永别了似的感觉笼罩着我。事实上,这是我们大家族这一个月来经历折磨的高潮;尽管您没有告诉我,但我从弟弟阿布都热依木勉强告诉我家里来了‘亲人’之口气,知道弟弟被迫给安排进家里的、一家没有信仰的无耻陌生人当奴隶;当我问您:“那个不要脸的客人还在吗?”时,您以一个深深的叹息转移了话题。
中国殖民者的迫害,自1949年东突厥斯坦被占领起,就以各种名义在持续;为了使我们屈服,殖民者先是没收了,继承了几代从事运输商贸的太爷爷伊迪里斯的马匹牲畜,拆毁了建筑宏伟的庭院房屋,瓜分了满园果树的果园,但您们没有害怕,没有屈服;因为尽管我们失去了祖国,但避风挡雨的家还在,在家里,我们是自由的;现在,这群野蛮、暴虐的殖民者,闯进了捍卫我们尊严、正直和良心的最后堡垒——家;这使您窒息,对吗,妈妈?辛劳父亲忍辱负重的叹息,妹妹们的屈辱,善良弟弟阿布都热依木如奴隶般的忍气吞声,使您备受煎熬,是吗,妈妈?您那些天真孙儿女可见的悲剧未来,使您恐惧,是吗,妈妈?您的爱,不仅滋润了我们,也延伸到了邻里朋友们的儿女,妈妈;我知道您很坚强,知道您坚韧地熬过了多少个风风雨雨,亲爱的妈妈;是什么样的迫害,使我的母亲恐惧、喊叫?这令人恐惧、笼罩祖国各地的戚戚黑暗让您忧心忡忡,是吗,妈妈?您是否难于忍受以族人的信仰、《古兰经》、乐善好施闻名遐迩,成为乐观、积极向上人生、文明桥梁之地的这一可爱土地,现在变成一块儿令人窒息的“苦难之地“?
自和您的联系中断后,我烦恼,妈妈;我被痛苦折磨,沉默;我六神无主,有时失神;偶尔不知身在何处,精神消沉;但,我没有放弃,不停地向万能的主祈祷。大约过了100多天之后,一位亲戚自中国内地省份给我发来了信息,得知弟弟阿布都热依木被判了21年在乌鲁木齐第一监狱服刑,妹妹们都被抓进了集中营;他告诉我,甚至没有人知道您和父亲的下落;他最后告诉我,我们家空无一人大门锁着;当我打听家里孙字辈时,他告诉他不知道。妈妈,弟弟阿布都热依木曾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以自己的店铺维持着兄弟几家的开支;妈妈,他那里都不愿去,只为尽孝伺候父老;我不知道弟弟们的儿女在哪儿?祸不单行,这噩耗使我更加痛苦、无助,亲爱的妈妈;我这里朋友们的亲人也被抓进集中营的消息开始传来了,妈妈。
亲爱的妈妈,我还记得您当年说的话:“如果有一天,边境被关闭、无路可通时,不要为我们担心,如往常我们会为你履行宰牲节义务,继续你保护家园的事业。“,现在我更深刻的理解了您的话,更明白您的远见卓识;在这一艰难岁月里,幸好我勇敢爱国的妻子茹贤·阿巴斯在身边;她如战友、如知心朋友陪伴着我;我们夫妻俩,一直在为成千上万无辜被抓捕着呼吁呐喊,寻求拯救之路;东突厥斯坦有几百万人被抓进了监狱、集中营,但世界各国媒体如倒扣巨大黑锅下的黑洞没有回声。
我和一战友们一起,夜以继日探讨民族拯救之路;我们寻找如何使世界关注我们,如何阻止中国殖民者最后解决维吾尔人的邪恶计划,我们制定了工作计划;2017年11月12日,您的儿子,作为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起者之一,参加了在德国召开的该会特别代表大会;我们夫妻俩都参加了会议;我被选举为世维会总检察长;我们夫妻俩白天连着晚上寻求民族拯救之路;您的女儿茹贤整天坐在电脑前向认识不认识的记者发信息,介绍我们面临的危机;她在为您及和您一样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呼吁,她不停地向美国国会议员们诉说我们的危机、面临的种族屠杀,并要求他们阻止这一邪恶;2018年3月15日,您的女儿茹贤和她的几个女伙伴们一起,发起了“同一个声音,共同的步伐“为题的全球维吾尔妇女抗议活动;我们夫妻俩,走访了很多个国家,参加了无数次的游行、集会,研讨会,以讲述我们民族的遭遇;当时,我和您的联络中断大约有400多天了,我得不到任何有关您和父亲的情况,妈妈;维吾尔人之外的,当我告诉他们”中国截断了我和父母的联系,我联络不上他们“时,他们都以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妈妈,我想念你们,越是想念你们,越痛苦;特别是想到一直在悉心照料你们的弟弟阿布都热依木,我脑袋冒火。
亲爱的妈妈,邪恶的中共政权剥夺了您及和您一样成千上万无辜兄弟姐妹做人的尊严,他们不分老幼、男女抓捕入狱、关进集中营,使成千上万孩子成为孤儿;妈妈,我们通过世维会,以及几年前我们组建的“维吾尔运动“向世界揭露了中共这一罪恶。2018年9月5日,当我们之间的联络中断约500天时,您的女儿茹贤在美国一家重要智库演讲:”我们在失去与父母、亲人及其儿女的联络;我们担心他们被抓捕,担心儿童幼儿被关进孤儿院,有近百万人被关进了集中营。“试图以此呼吁美国帮助维吾尔人;过了六天之后,邪恶的中国政府就将茹贤的同胞姐姐古丽仙在乌鲁木齐抓捕,把她已是60多岁高龄在阿图什的婶婶也当作人质抓了起来了。
亲爱的妈妈,如果您看到爱憎分明,不欺软怕硬,帮助弱者,勇于面对强权的,和您一个性格的茹贤,如果您看到她是如何质问中国政府“我姐姐在哪儿?我父母在哪儿?我亲人在哪儿?成千上万维吾尔人在哪儿?”的那一幕,您一定会说:“我的好闺女,谢谢你。”而且,相信您会为她更坚定地继续而祈祷;母亲,我特别想念您,特别想念您的声音和话语;我特别想告诉您,您的女儿茹贤,因在有美国总统川普、副总统潘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国务卿庞培奥及美国其他高级领导人、外交官和众多媒体的场合为维吾尔人呼吁而受到了奖励,我特别想告诉您这一切;我相信,您一定会为此而非常自豪,我想看到您抬头挺胸满脸笑容的神态,妈妈。
亲爱的妈妈,和您的联系中断后,我以回忆过去试图忘却痛苦;越回忆越为有你们这样勤劳,勇敢,善良、耐心的父母亲而倍感自豪;你们为了使穆罕默德圣人所传伊斯兰在东突厥斯坦持续下去,而省吃俭用把我送到了那些因为信仰而做过二三十年牢的前辈伊斯兰学者那里,以继续他们开创的事业;当我在国外时,你们又不远万里来看望我,还连带慰问我的同学们。
亲爱的妈妈,我们夫妻俩无论是在聚会、访谈、旅行、还是与会、参加游行示威、演讲,与伊斯兰团体交流、在清真寺、大学,都在为你们及东突厥斯坦的全体苦难者发声;为拯救苦难中的祖国,我们奔走于日本、澳大利亚,土耳其、加拿大,欧洲及我们住的美国每一个州几乎都走过来了,妈妈;为了不使神圣的东突厥斯坦的伊斯兰之声中断,为了不使爱好自由的维吾尔民族精神被征服,为了让牢狱高墙倒塌、集中营关闭,苦难结束,使东突厥斯坦完全独立,人民自由,使人民能享受信仰自由和丰衣足食的欢乐,无数维吾尔人组成了民族复兴的滚滚洪流,我们在此奋斗队伍中在尽自己的一份努力;这就是我们在年轻气盛时,在阿拉法特山、在埃及商讨的:“向西迁徙”信念的一部分;因为此理想,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了维吾尔社团,而且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了为维吾尔人发声的组织,这是真主的安排,我感谢主,妈妈。
今年,当我们在加拿大渥太华搞活动时,和住在那里的张晓文先生见了面;他是第一个使用卫星地图发现东突厥斯坦集中营的人,并成为了世界有名的集中营专家。
亲爱的妈妈,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们要求他用卫星找到我家,他问我:“你家在那个城市?”我说:“和田市拉斯克镇阿胡伊村。”他用很大的电视屏幕让我看了我们村;先是波斯坦村,然后是伯格土格曼麻扎,再往后沿着沙漠找到了我们家;我见到了离家34年再也没有见过的家,妈妈,那一瞬间,我真想跨越屏幕进入我们家和你们团聚;当时我心跳加剧,眼含泪水试图找到你们,但找不到,妈妈;我又问张晓文:“离我家最近的集中营在哪儿?”他立即沿着我们村水库穿越,在汗埃里克以北、新艾力克以西、拉斯科西北、新阿瓦提沙漠中,找出了一个庞大的集中营建筑群;他给我们讲说集中营还在扩建,并指出了2019年12月29日新附加的集中营;我猜想我大多数亲人可能都在这集中营里,我不敢想象这个集中营里的妹妹们在经历何种的苦难;但是母亲,我不知道您在哪儿?父亲在哪儿?我急忙问张晓文孤儿院在哪儿?他指给我拉斯克村工厂附近像监狱的建筑物;他还给我们找到了我妻子茹贤在乌鲁木齐的家,以及她家附近使馆清真寺的三D图像;然而,我们知道古丽仙姐姐并不在家;她在哪儿,我们不知道,妈妈;顿时,妻子茹贤沉浸在悲哀中;我们也没有找到善良的古丽仙姐姐;通过眼前的大屏幕,我们看到了布满东突厥斯坦的大大小小集中营;他甚至给我们看了比达坂城城区还大的达坂城集中营,以及可能是世界最大之一的乌鲁木齐监狱。
亲爱的妈妈,不知道自武汉肇始的中国病毒又给你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厄运?不知您怎么样?不知您是否有吃的和喝的?最近,自和田及东突厥斯坦各地强制向中国各省运送维吾尔青年男女奴工中不知道有几个我的妹妹和弟弟在;我那些幼小的侄儿女又不知在哪个角落在哭泣,又不知那个弟弟做了器官移植的牺牲品?我最亲爱的弟弟阿布都热依木不知是否被转到了中国其他省份的监狱?说实话,亲爱的妈妈,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哪一位活着,哪一位已经归真了;但我希望,你们全部都好好活着;我祈求真主,在此斋月,向你们、向全体东突厥斯坦民众及全世界赐予丰富、宽恕、博爱和拯救。
亲爱的妈妈,据《古兰经》,凡是和真主作对的独裁者都不得善终;这个中国独裁者也一样逃不脱失败的命运;在东突厥斯坦各个角落,如我母亲您——布维玛丽亚姆一样,在斋月的凌晨早早起来,坐在礼拜毯上向真主哭诉的成千上万维吾尔母亲的祈祷,真主一定会接受;我们一定会获得拯救;暗夜之后必然是黎明;真理显现,暴政必然灭亡。
我们俩也一定会再相见团聚,妈妈;不在此世,就在来世!
您的儿子,
阿布力克木伊德利斯 (Abdulhakim Idris) 于华盛顿敬上。
2020年4月25日。